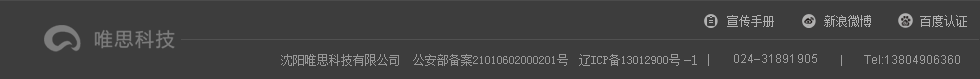編者按:幾十年前,一張《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照片成為了一項對互聯網意義深遠的技術的樣本。她是計算機工程師眼里的神話人物,是互聯網的“第一夫人”。但是最近又成為了被激烈爭論的技術原罪的客體。她究竟是誰?她有著什么樣的人生?《連線》雜志設法尋訪到了現已67歲的封面女郎,為我們揭開JPEG守護神的秘密。

左:當年的Lena;右:現在的Lena
每天早上,Lena Forsen都會在專門為“互聯網第一夫人”定制的一口黃銅木制座鐘之下醒來。
這口鐘是20多年前由圖像科學與技術學會(Society for Ima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贈送給她的,以紀念她在塑造我們所熟知的數字世界當中無意間扮演的關鍵角色。
在一些計算機工程師看來,Lena是一個神話人物,一個相當于Woz(蘋果聯合創始人沃茲尼亞克)或者Zuck(扎克伯格)的名人。不管你認不認得她的臉,你都已經使用過她幫助創建出來的技術;幾乎你拍的每一張照片,訪問過的每一個網站,分享的每一個迷因等,都欠了Lena一點點的債。但時至今日,作為一個生活在自己國家瑞典的一位67歲的退休人員,她仍然對自己的名聲感到有點困惑。“我只是很奇怪這怎么就沒完沒了了呢。”
Lena的偶像之路始于《花花公子》的頁面。1972年,21歲的時候,她以十一月女郎的身份出現在雜志上,除了一頂太陽帽、一雙靴子、一對長襪以及一條粉色圍巾以外什么都沒穿。
大約6個月后,一份同期的雜志出現在了南加州大學信號與圖像處理學院,當時Alexander Sawchuk和他的團隊正在找一張新的照片來測試他們最新的壓縮算法——這種算法會使得笨拙的圖像文件變得容易管理。而Lena在《花花公子》上的那張照片,由于有著復雜的顏色和紋理,成為了完美的候選。他們撕掉了頭1/3之后,對其進行了一系列的模數轉換,然后將512行掃描的結果保存到Hewlett-Packard 2100上。
USC非常自豪地將結果的拷貝交給實驗室訪客看,很快,這位扭頭越過香肩風情萬種地望著你的年輕模特的圖像就成為了一項行業標準,經過數十億次的復制或分析之后終于變成了我們今日所熟知的JPEG圖像。據伊利諾伊大學工程學院的編輯James Hutchinson說,Lena對于工程師而言,相當于“麗塔·海華斯之于二戰時躲在戰壕里的美國大兵。”
他們為她寫詩,給她的肖像添加優美的花紋,還給她的照片插頁起了個昵稱:“The Lenna”,給人以文藝復興肖像畫的感覺。在1973年的電影《Sleeper(沉睡者)》里,當主角在2173年醒來時,他被要求辨認過去的一組圖片,其中就包括了斯大林、戴高樂以及Lena的照片。這些日子以來,盡管她的圖像大多數是出現在媒體研究摘要以及碼農的論壇上,但被普遍認為是互聯網史不可磨滅的一部分。
不過Lenna成為論戰的來源的歷史,幾乎跟她被計算機科學家當作偶像崇拜的歷史一樣長。羅徹斯特理工學院院長David C. Munson爵士在1996年的時候寫道:“我曾聽說女權主義者提出這個圖像應該退役了。”但19年后,Lenna依然非常普遍,以至于弗吉尼亞州的高中畢業生Maddie Zug都不得不在《華盛頓郵報》上寫一篇專欄。她解釋說,這張圖像引起了她所在班級男生的“性評論”,把它繼續放在課程里面已經成為一個更廣泛的“文化問題”的證據了。
UCLA的數學教授Deanna Needell也有類似的大學回憶,2013年她和同事進行了一次無聲的抗議:她們買下了男模Fabio Lanzoni大頭照的版權,然后用來替代Lenna的作為其圖像研究對象。不過最嚴厲的批評也許來自于《Brotopia(男性烏托邦:摧毀硅谷男孩俱樂部)》的作者Emily Chang(彭博女主播)。她在開篇中寫道:“Lena照片的使用泛濫可被視為技術產業內部行為的一種先兆。在今天的硅谷,女性是二等公民,而大多數男性對此視而不見。”在Chang看來,Lena的裸照被撕下然后掃描的那一刻是“技術原罪”的標志。
不過這場關于lenna的論戰里面顯然少了一個人的聲音,那就是Lena本人。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開口已經是1997年的事情了,就在那次會議上她被授予了自己那個心愛的座鐘。
據前圖像科學與技術學會分會會長Jeff Seideman回憶,Lena的出席引起了他的同事的一陣騷動。他告訴我說:“雖說聽起來很蠢,但他們都很吃驚她居然是個真人。而且其中一些人看她的照片都看了有25年齡,她已經變成了那幅測試圖像了。”從此,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上出現了數十億用戶,數萬億的照片,已經沒有人再關心她對自己那張照片及其爭議性的來生的看法了。
我是在一年前開始尋找Lena的。作為第一夫人,她出奇的難找。經過一系列徒勞無功的搜尋之后,我發現她最后一次公開露面是在2015年,所謂“特邀嘉賓”出席魁北克城舉辦的一場圖像處理會議。活動照片顯示,她在耀眼的年輕的自己的投影下登上了講臺。我聯系了會議組織者,對方說他們已沒有她的聯系信息,那個安排她參會的人已經死了。最后會議主席Jean-Luc Dugelay同意幫助我聯系lenna。不過他警告說,Lena可能會拒絕見我。他寫道:“她現在不想跟這一切有任何瓜葛。”
在斯德哥爾摩一個悶熱的夏日,這個技術原罪的客體就是這么向我走來的。她讓我到Stureplan跟她見面,那是一個熱鬧的中央廣場,位于這座首都的一個高尚社區之內。我在一個大型的蘑菇狀公共雕塑下面等著,因為那里有我迫切需要的遮蔭。附近的一棟建筑上,數字公告牌閃現著三星S9+的廣告,展示著它那銳利的攝像頭。
很快,兩位年紀比較大的女性出現在一條小巷。Lena帶了一位朋友過來,我想應該是為了確保我是個安全的對話者。她身穿黑白相間的太陽裙和一雙粉色的勃肯鞋。她把白發往兩側裁短了,逐漸收斂成優雅的穗狀,閃亮的修剪過的指甲跟她的鞋子顯然很搭。“我是Lena,”她說著,伸出了她的手:“有什么可以幫你的?”我們一起步入到附近的一個高端商場里面,在一家時尚的咖啡廳找了個安靜的角落坐了下來。
我們從開始談起。在高中畢業后,Lena就搬到美國以互惠生的身份替她的一位親戚工作。她打算在那里呆一年,但后來變成了8年。到了1971年時,新婚的她在芝加哥住了下來,努力想讓自己收支相抵。她當時的丈夫鼓勵她去跟一家當地的模特公司簽約。“我不夠高,沒法做很多的時裝表演,不過我做了一些珠寶和平面模特的活,然后就跟《花花公子》聯系上了,”她說:“他們希望我能給他們做個封面。”然后被介紹給了一位叫做Dwight Hooker的攝影師,后者問她對拍點“花花公子照片”有沒有興趣。她告訴我說:“其實我對這個一點概念都沒有。但我的丈夫卻認為這很酷,而且還有錢拿,當時我又沒有多少錢。”
在她的裸照插頁出版后,Lena已經拿到了綠卡,隨后又離婚找了一位新男友。《花花公子》邀請她去Hugh Hefner(《花花公子》老板)的比弗利山莊府邸,但她拒絕了。她解釋說:“我們都得去那里看望身穿長袍的Hefner。他想讓我去加州,但我不感興趣。我沒這方面的抱負。”
相反,她跟男友一起搬到了紐約羅契斯特,找了一份柯達模特的工作。她成為公司的一名“Shirleys”——也就是照片用來校正彩色膠卷的漂亮女性。(這個綽號出自第一個擔任該角色的女性,Shirley Page。)這是一份很輕松的零工,所以Lena還有時間在一些晚上到本地的萬豪酒店當酒保。
在那個時期的一張照片里面,她拿著一本書非常優雅地坐在420型柯達Readymatic Processor旁邊。在另一張照片中,她在1973年的柯達《攝影》封面微笑著,手里拿著一個攝像機和麥克風。《施樂7700使用手冊》的封面是大眼睛的Lena疊加到一臺復印機的圖片上,仿佛就是從機器里面冒出來一樣。

1970年代,Forsen的職業是模特。她的照片最后出現在了柯達、施樂等圖像相關產品的目錄上,而她著名的《花花公子》照片成為了一篇圖像處理博士論文的插圖。
事實上,Lena的照片在歷史的這一特定時刻傳播得那么廣泛很難說是巧合。20世紀上半葉,隨著計算的地位從下等工作變成更需要腦力的、更男性化的職業,一小群搞所謂的計算機的女性正在成批離開技術產業。
技術史學家,《Programmed Inequality(寫入程序的不平等)》作者Marie Hicks說:“1973年,當她的照片被帶進實驗室時,哪怕沒有上千也有數百的女性被推出去了。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個。哪怕他們不用《花花公子》的插頁,也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會用另一張漂亮白人女性的照片。因為是《花花公子》而引起了我們的關注,但其實真正重要的是計算從一開始的世界建構——這是為一部分人打造的世界,而不是另一部分人的。
通過為《花花公子》和柯達工作,Lena在繆斯、過去與現在之間結成了一種非常特別的姐妹關系。這個故事是這樣的,19世紀末,有人在賽納河畔打撈上來一具少女的遺體,深受其美貌觸動的巴黎殯葬師給她制作了死亡面具并開始售賣復制品。于是她就有了塞納河的無名少女的美名。她的面具給20世紀上半葉的藝術家和小說家帶來了靈感,還被用來作為急救訓練用人偶模特。
類似地,在20世紀初時,模特Audrey Munson的身體也被全世界復制為鋼鐵和大理石雕像。盡管在她短暫的職業生涯的巔峰時她非常有名,但很快就淡出公眾視野直到死去。不過她的形象依然活著:以匿名的方式。Munson的肖像依然裝點著紐約的很多橋梁和建筑,但直到最近還沒有人知道她的故事。
不管是Munson還是無名少女,她們都是成百上千肖像被用來校正20世紀攝影與膠片色彩的女性的先驅。這些女性的身份塑造了其身體被用來創造出來的技術:比如說1950年代柯達首次開始雇用Shirleys時,白人女性占據了壓倒性的位置,其結果是膚色更深的人被柯達膠卷忠實地捕捉下來的可能性降低。(到了1990年代時,柯達開始雇用多種族的Shirleys)與此同時,Shirley Page已經從政府的備案記錄中消失,NPR用了好幾個月想找到她,結果徒勞無功。
這一趨勢延續到了本世紀。Suzanne Vega并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會被用來創建第一款MP3,直到一天一位父親在她孩子的幼兒園向她表示祝賀,因為她是“MP3之母”。20年后,配音演員Susan Bennett收到了一位朋友的電話,因為對方想知道為什么蘋果新的語音助手的聲音聽起來那么熟悉,后來才知道原來Bennett就是Siri。管中窺豹就可以看出這些女性的面孔和聲音已經如何根植到技術里面,即便她們的名字和生活如此經常地被人所忽視。
Lena自己仍然對自己的肖像發生的事情感到困惑。她回憶道:“我在魁北克的時候,這個女孩走過來對我說,‘我想我認得你臉上的每一塊雀斑,’她那意思就好像‘哦,原來你是真的啊。你真是個人啊。’這太瘋狂了。”但當她講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回憶從美國回到瑞典,談起自己的婚姻和工作,說到她的孩子和孫子的生活時,很顯然《花花公子》以及后面的事情只是一個好奇的注腳,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要是沒人想起要告訴她這一切的話,她基本上已將這段經歷排除在外。
當我問她是否聽說過最近關于她肖像的爭議時,她似乎對自己會在傷害或者令年輕女性氣餒的事情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感到震驚。我發了一些關于Lenna的文章給她看,隨后又給她打電話想看看她有什么看法。她說那張照片其實沒露多少,只是到肩膀的位置,所以她很難看出這有什么大不了的。Lena說:“我看了那篇班上的女孩跟那些男生的文章時,我能理解因為她是班上唯一的女生。也許他們看的是整張照片。”

Forsen,攝于2019年1月13日她的家中
Lena對Sawchuk及其模仿者沒有半點怨恨,那些人都很欣賞她的照片;她表達的唯一遺憾是自己沒有得到更好的補償。在她看來,這張照片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她說:“我對那張照片真的感到非常自豪。”
她有這種感受是完全說得過去的:跟技術業的很多女性不一樣,Lena因為自己的貢獻至少得到了承認,甚至受到了款待。Hicks說:“她拍了照片,然后大家開始以這種優雅的新方式使用這張照片,而現在她已經被融入到機器的設計當中,有點永生的味道了。這就是為什么一些擔心技術偏見的人覺得這個有問題的原因。這是一套圍繞著特定權力關系刻意設計的系統。”
就像Lena的身份被排除在Lenna以外一樣,Lenna也不再像是真實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幾十年歲月的光陰已經令具體細節模糊,當年的時光已經越來越難以回憶,唯有她的肖像被一代又一代的工程師渲染得愈加豐富。
她在瑞典試圖去看看有關Lenna的內容但慢慢就讀不下去了。“這跟我距離太遙遠了,”她說。她的兒子倒是從事技術工作,偶爾也會試圖向自己跌母親解釋一下她的照片是如何被使用以及用到何種程度的。她說:“他跟像素打交道。我不懂這些,但我想我還是做了點貢獻的。”